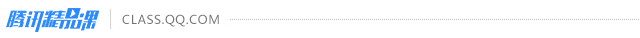從閱讀與寫作的關系上來看,讀書多的人絕大部分是會寫作的人,而一個能寫出很好的作品的人更不可能不愛讀書。這只因在看了足夠數量的文化精品后,哪怕只是東家模仿一點、西家拼湊一點、再加上一點點自己的領悟與潤色,最后拿出來的成品,也足以令許多人拍案叫好。
我寫作的一個特點是引用多。高三下學期語文老師的女兒為我們班的期中作文寫點評,她數了我54分的作文里引例的數量,有接近二十個,有直接引用也有化用。這些引例都是平時我從閱讀中積累下的東西,也就是說在一千一百字的篇幅中我每寫五六十個字就會用到我的閱讀成果。
這里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篇作文里同樣是大量引用,有的人的作文會被評價為“豐富”,有的人則是“雜亂”、“堆砌”。為什么?我覺得這是對作文中所引用的內容理解程度的差異造成的。同樣的東西,有的人是在閱讀中看來、研究并思考過的,有的人是從類似《高中生議論文論點論據大全》中看來的;前者是深入理解,后者則只得了個皮毛。
比方說,同樣引用尼采,有的人寫“尼采,這個偉大的哲學家教會我一種高貴的精神”;而有的人直接引用他的作品《蘇魯支語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寫道:“‘太陽!若無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光輝為何?’,由是開始了蘇魯支的墮落,亦開始了尼采在這世間無止境的追求。他像蘇魯支一樣為世界奉獻著他的熱愛與智慧,也像蘇魯支一樣不斷經受著世俗的冷笑與中傷。尼采,這個‘瘋子’、這個智者,從來沒有放棄,也沒有停止過他的追尋。”
孰優孰劣,不言而喻。
閱讀對于寫作而言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提供模仿的條件。
我最早開始寫東西,正是始于閱讀中的模仿,不管是何種作家,只要我覺得好,我就會按他的風格仿寫。小學時我就開始有意識地在我的作文中學習一些冰心兒童文學獎獲獎者的風格,后來讀的書更多也更雜,我能記起來自己模仿過的作家有魯迅、夏目漱石、郭敬明、村上春樹、錢鐘書、杜拉斯、三毛……還有一些恐怕是忘記了。我還自己寫古典詩詞,甚至模仿司馬遷為自己寫了一篇文言文小傳,可惜沒能保留下來。
在模仿這些個性鮮明的作家的過程中,我慢慢開始有了自己的風格。我是怎么發現這一點的呢?這得歸功于我的癖好,那就是寫了點什么就想給人看。
4
創作
到這時我就知道,這是我寫作的第二個階段了,我在從模仿走向創作。
寫東西寫得好,與其說是天賦,倒不如說是熟能生巧,就像做飯、洗衣服、開車一樣。我現在寫文章很少構思或查證,筆到文來,半小時之內在電腦上完成千來字的短文對今天的我來說根本不叫事。但這背后呢,是我從初中起每天不間斷的練筆。
作文是很靈活的東西,當判卷人看到你能用文言文不出錯地寫一千多字、或者你的語言像詩歌和散文一樣漂亮時,他對議論本身的標準就會有所放松。作文考的歸根結底是文學水平而不是議論水平,換言之只要你能體現出你的水平高,實在不必太拘泥于文體與所謂的標準。高考前我拿著自己高三下學期的作文看,二十多篇教師打過分的作文中我拿到50分以上的至少有二十篇,其中有一篇滿分,還有不少55分、58分。這就是我說的一切最好的證明。
只要能運用語言去傳遞你想要送給這個世界的東西,那么,你在這門語言上的學習就是成功的。
語言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應該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我們學習語言是為了什么?為了在考試中拿好看的分數?為了考各種各樣的語言能力認定證書?為了自豪地告訴別人這個字我認得?
如果對于上面的問題一個人的答案是“是”,那么,他已經忘記了語言這種東西產生的初衷。
語言,是為了表達,是為了表達精神,是為了為這個世界表達愛、表達美、表達動力、表達希望。讀那些經典的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無論國家、無論時代,那些作品所擁有的打動人的力量絕不是因為它的文字有多么華麗、布局有多么復雜、詞語有多么精準,而是由于它其中蘊含著人類最為高貴的、永不過時的某種精神。
有很多成功的作家,他們出道時接受文化教育的水平絕不比現在的中學生要高,讓他們去做我們的考卷,他們不會有比大部分普通高考生更能看的分數。但為什么他們可以成為語言大師、文學巨匠?是因為他們能夠抓住語言的內核,他們知道該如何運用語言去表達,也知道應當用語言表達些什么。
只要能運用語言去傳遞你想要送給這個世界的東西,那么,你在這門語言上的學習就是成功的。
誠然,我有個很不錯的語文分數,然而這確實是有很大運氣成分在里面的。我的語基很薄弱,高中時我是班里有名的白字先生。如果換一套題,我可能會連著錯前三道選擇,就像我在之前的考試中有過的那樣。
但是,我從未因為我在任何一次考試中的分數而懷疑自己在語文這門學科、在中文這門語言上的能力,我最自豪的絕不是我是北京市的語文狀元,而是我能夠如我所愿地運用文字——這才是學習語文真正帶給我的、令我感激的禮物。
這才是我為什么熱愛語文。